 一次,有幸與廣州廣告協會的幾位主要成員相聚。他們覺得香港位於廣州鄰旁,文化相似,相信香港的廣告發展史,可能會帶來國內同業們一點啟示。其實香港的廣告業,早於十多年前,開始回歸祖國探索。現將一些過往香港廣告業媒介發展史的一些見聞,與大家分享。
一次,有幸與廣州廣告協會的幾位主要成員相聚。他們覺得香港位於廣州鄰旁,文化相似,相信香港的廣告發展史,可能會帶來國內同業們一點啟示。其實香港的廣告業,早於十多年前,開始回歸祖國探索。現將一些過往香港廣告業媒介發展史的一些見聞,與大家分享。
鱔稿的由來及轉化
許多人都想利用新聞發佈來協助宣傳,或製造另類宣傳手法。其實內裡是有一套專門技巧。
在香港,新聞稿被稱為「鱔稿」。原來,許多年前,香港當時的生活並不富裕,想出新聞稿,往往一頓飯便可解決問題。傳聞中,當時報館多位於香港中上環一帶。那裡有一家食府,以吃鱔為名。因利成便,許多人便在食府請報館吃飯。當然在菜單上,少不免吃鱔。故此,新聞稿俗稱為「鱔稿」,出新聞稿就俗稱「當大鱔」。時至今日,雖然生活富裕了,工作規範化了,加上香港成立了廉政專員公署,請吃鱔的事情不再發生,但許多客戶仍舊出新聞稿。
通常,客戶利用其廣告投放量,去報刊洽談,而報刊為免得失客戶,故此許多報刊都設立「商人商事」、「商業快訊」等等的專欄,去滿足客戶的要求,又可讓新聞部有自主權去刪改,亦讓讀者知道此乃商業訊息而非一般的新聞。如果客戶需要多出幾次的話,他們亦可以以廣告形式刊登。不過,要在文件說明此乃廣告,所以,今天的鱔稿,不含半塊鱔肉,而是一種有高透明度和有規範的商業活動。
銷售核數助廣告效益
外國人有一句話叫:「As simple as ABC」,意思指事物有如ABC那麼簡單。
記得,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企業自辦的廣告公司工作。一次,有一客戶欠錢,所以要利用小錢債法入稟法院。上庭前,經理突然不能出席,要由我充擔原告角色。初出茅廬的我,一踏入法庭上,便已六神無主。
一開始,法官要我講述我在公司的職責。我說我是主管媒介的(其實當時媒介部只有我一個人)。法官見我年青,不大相信我是部門主管,立時劈問我知不知甚麼叫ABC。當時的我,完全不知ABC與媒介的關係,所以只有說不知。那時,法官說他十分鄙視連ABC 也不懂的人,差點兒不准我代表公司作證告人。
此事之後,我立心去加入更大的廣告公司,至少可以知道甚麼叫ABC。
原來ABC是「報刊銷售量核數公證會」(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的縮稱。在許多國家,都有ABC這個會。大部分的ABC主要成員,是來自當地的出版人協會、廣告主協會(2A's)、廣告代理商會(4A's)。目的是聯合釐定指標,提供給一些認可的核數師,以作核對報刊銷量數字的劃一准則,讓公眾、廣告主、廣告代理及其同業們,提供一個可靠及有高透明度的銷量核數及分析。在分析中,他們會很清楚看到每份報刊,在何時何地用何法銷售給何人,售價是否合乎標準。
在推動ABC概念時,我們在香港曾舉行一個打擊非核數刊物的虛報數字的調查研究。我們在全港的報攤,隨機抽樣調查,發現許多報刊的自報數字,竟與調查結果有十多倍的分別,證明虛報情況甚為嚴重。
從廣告代理立場來看,媒介指數雖能反映部分普及性的媒介的讀者數量及成份,但不足以幫助我們去探索個別趣味性或專門性媒介的量性效果。甚至在媒介指數有包括的媒介裡,亦不能反映出它們在海外或中國國內銷售量及其影響性。
甚至有了讀者數字,配合本地銷售數字,便可以推算到每份刊物的平均讀者人數,而可以幫助我們看到其它廣告效益。以前,香港報刊的銷量核數,是由英國ABC主理的。但自一九九四年開始,香港已成立其ABC,務求本地化及加以推廣。
電腦化與跑媒介
在七十年代末期,廣告業開始關注及大力推行媒介調查研究。不過當時因私人電腦仍沒有普及,所以我們只能將一疊疊印得密密麻麻的電腦數字,翻來覆去,找出有關的媒介數據。當做到通宵達旦,神志迷糊時,那些密麻麻的數字就如一大堆小蚊子,在你眼前飛來飛去,而你要在群蚊中,捉你要的蚊子。所以當時我們俗稱此為「捉蚊子」。
當其時,有許多前輩對數字始終抗拒,很快就不能立足於廣告界中。另一批被淘汰的廣告人,是後來對電腦有排斥的前輩。
八十年代中期,有多間國際廣告公司採用電腦。當時的電腦比今天的雖然簡單,但運用起來,卻複雜得多,所以公司要指定受過培訓的人,才可以接觸昂貴的電腦。
有一次,我發現一位電腦操作員,沒有關上電腦便下了班,我只有不停的致電到她家中,直至深夜才找到她,從電話中知道如何可以把電腦關上。今天,科技先進很多,許多人都懂得開關電腦,把媒介調查研究大力推廣電腦化。
許多同業新進,在國內聽到當媒介員常要「跑」媒介,覺得莫名其妙。不過,對我這個早於七十年代末期加入媒介行業的人,聽來反而有點懷舊味,不禁回憶當年的香港媒介員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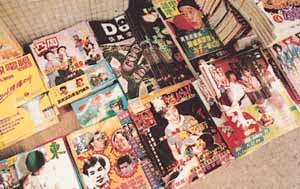 當時,我在一家十分細小的廣告公司幹活,只有較先進或較弱的媒介,才會找到我們的門上。一般來說,我們也要去跑媒介。後來,電視廣告業興盛,再加上當時香港多了一家新的電視台出現,競爭更為激烈。電視台率先大量聘請及培訓廣告業務員,實行分秒必爭去爭取每一分的廣告投放。同時,亦迫本來獨佔鰲頭的報紙廣告人,為力保自己的江山,也需要主動地跑到廣告代理及廣告主的門前促銷自己的媒介或打打關係。
當時,我在一家十分細小的廣告公司幹活,只有較先進或較弱的媒介,才會找到我們的門上。一般來說,我們也要去跑媒介。後來,電視廣告業興盛,再加上當時香港多了一家新的電視台出現,競爭更為激烈。電視台率先大量聘請及培訓廣告業務員,實行分秒必爭去爭取每一分的廣告投放。同時,亦迫本來獨佔鰲頭的報紙廣告人,為力保自己的江山,也需要主動地跑到廣告代理及廣告主的門前促銷自己的媒介或打打關係。
發展到今天已不再需要跑媒介了。如果我們需要「跑」到媒介主的辦公室時,那只有大宴會或嚴重的問題出現。
步向規範趕走腐朽
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經濟蓬勃,但廣告業的專業化仍未達到應有的水平,更有些前輩利用他們的職權,混水摸魚,淘得私人利潤。當時,香港已有廉政專員公署,亦已將廉政推廣到非官方機構去。為了不違犯賄賂條例,故此,有人利用麻將桌上來作交易。據聞,有些前輩差不多每天都四時下班去了,要去酒家與媒介打打關係,其實是與媒介打打麻將才對。有些前輩更因麻將術不高,或沒有耐性在麻將桌前呆足一個晚上,所以,不如每每馬馬虎虎大叫一聲:「我糊了!」然後將麻將蓋下推亂,干脆說收錢罷了,情況十分腐朽。
後來,調查研究被推廣,在有意識競爭下,只有強者能居之是必然的事。媒介主、廣告主和廣告代理都一同理解此生存之道。所以,只將廣告投放在有效益的媒介上,而媒介主亦集中精力去保持或爭取更多的讀者或觀眾,弄成一切規範化,走上正軌。
之前的腐朽情況,我想是由以下四大原因所弄成的:
(一)廣告主(指當權者而不一定是老闆)沒有設想將廣告變成一種有效的投資,而是交待了事。其實,有效的廣告投放,是用較少的廣告投放預算,去「賺取」較大的廣告效益。廣告是投資,而不是花費。許多客戶仍沒有想通此道理的。拓展市場,廣告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二)廣告代理許多時沒有視此為一專業性服務,以為跟幾個媒介主相熟,取得一點方便或更大的折扣,便可以成為廣告代理。其實他們只不過是依附在廣告主及媒介主身上的一條寄生蟲。除了折扣和某些方便外,他們根本對整體廣告策劃上沒有貢獻。
(三)許多媒介是由文人掌管的,談到金錢方面,他們都只是交由一些「可靠」人士代為管理,沒有當作他們的廣告代管人是媒介的一部份,同步發展。他們沒想到廣告不但是媒介的生命錢之一,有規範的運作,是會帶來更大的效益,而且廣告的本身及運作的模式,可以大大影響媒介的形象及運作的。
(四)當局沒有大力協助和鼓勵業內人士的立法或監管。
踏出香港放眼神州
記得七十年代末期的廣告步向規範化,做廣告不再是單單劃劃圖的事情,令同業們都感到有自豪感。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隨著亞太區經濟飛躍,加上香港的天時地利人和,許多國際公司在香港設立亞太辦事處,亦有香港產品和服務,向海外大力推廣。從而令香港的廣告業亦因此而跳進亞太區,由亞太區跳進國際去。
在一九七九年,當第一期亞洲商人閱讀調查報告(Asian Profiles)推出之時,許多人都覺得主辦者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只是和人說夢話,作出與香港毫無相關的事情。誰知幾年後,各大廣告公司特地派人去鑽研其中的奧秘。於八三年,更有一間國際廣告公司,在港成立第一個專門做海外媒介投放的部門,惹起同業們一同競爭的主要項目之一。
海外投放除了帶來廣告公司更大和更多的金錢受益外,亦有助香港媒介從業員學到許多外國的東西,讓我們的專業學識,更上一層樓。
到八十年代末期,香港的情況有所改變,使部份的亞太廣告投放轉移往新加坡去。不過,又隨著換來一個更大的廣告市場——中國。當時各大廣告公司都設立中國廣告部,或在國內建立合資公司發展,為公司及客戶開拓中國市場。
我們一班老朋友常說,以前大家只聽過對方的名字,總是沒有機會碰面。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們常在海外媒介所舉辦的酒會中相識碰面。到今天,我們往往在國內的火車或飛機上遇見,短短十數年的變化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