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三個月前怒斥香港記者太年青、簡單及幼稚之後,江澤民又趁澳門回歸一週年,訓示傳媒要注意社會責任、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再次牽動香港傳媒的神經。究竟是否香港傳媒愈來愈沒有社會責任感,令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出面勸戒,還是中國領導人借故干預?面對江澤民的訓斥,香港傳媒又應如何自處?本文嘗試引入「公共空間」(publicsphere)這個概念,探討香港傳媒在「後殖民時期」(post-colonialperiod)的角色及它們與中央領導人的關係。
江澤民對傳媒的期望
江澤民的演詞說:「要求傳媒不僅要注重新聞自由,而且也要注重社會責任,在事關澳門(也適用於香港)繁榮穩定、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的問題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香港新聞界一定不喜歡這段演詞,但江澤民這番話是說出他一直以來對港澳傳媒的期望。以前這個期望放在心裡,現在「真情流露」,宣諸於口。
 江澤民曾嚴詞訓斥香港傳媒。 |
過去五十年,國內的傳媒一直遵從馬克思共產報業理論去運作,儘管近年市場力量抬頭,但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傳媒依然是政治工具,是黨和國家的喉舌,發揮宣傳、教育、組織及動員的作用。很明顯,江澤民的中國社會主義傳媒觀有別於西方的自由主義傳媒觀,認定傳媒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服務和為黨效勞。所以,他談的傳媒社會責任,自然是指社會主義式的社會責任,期望傳媒要照顧社會安定及國家政治利益,這種想法對中國國家領導人來說,是很理所當然的。
問題在於香港的傳媒,一向奉行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運作形式,所以傳媒擔任的角色與中國領導人的期望並不一致。其實中國領導人在理性上是了解到這個差別,並已盡量克制,在一國兩制的前題下包容香港傳媒。但在感性上他們不一定能完全接受,故在特殊情形下可能會一不留神而「滑邊」(江澤民用語)。上次江澤民情緒激動地教訓香港記者,大概屬這種情況。
 國內傳媒發揮黨政喉舌角色。 |
但今次江澤民有關社會責任論的講話,是在澳門回歸一週年的官式場合發表,看來不是說溜了嘴,而是想得很清楚之後寫下的。這反映到香港傳媒的表現,並非不符合中國領導人傳統期望那麼簡單,而是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了中國領導人包容的限度。他們覺得有需要站出來提點一下,以免香港傳媒成脫疆野馬。至於香港傳媒哪方面的表現出了問題,我們就只能猜測及推敲。有可能是香港傳媒批評特首太不留情面,損害到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也有可能是大肆報道遊行示威及支持修訂公安法,被認為威脅社會穩定。
傳媒「公共空間」
在今次「社會責任論」事件之中,其實江澤民在姿態上很低調,只是向傳媒「提點」,而非施壓,但畢竟他侵入了傳媒「公共空間」,所以引起了傳媒工作者的抗議。
在西方的社會政治思潮之中,「公共空間」是一個重要概念,它經過社會理論家哈貝馬(JurgenHabermas)的闡釋及發展,近年傳播學者也經常引用這個概念來探索傳媒與民主社會之間的關係。
在民主社會發展的初期,市民大眾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經常聚集一起,在咖啡店或公共會堂論政及討論社會事務,形成一個公共空間,醞釀民意,制止政府的施政。隨著人口劇增及社會複雜化,市民大眾不可能大規模走在一起,於是集會的場地搬到大眾傳媒,大家透過傳媒議政及表達民意,大眾傳媒成為現代公共空間的主要構成部份。談起公共空間,一般都是指大眾傳媒,尤其是它們的新聞報導,是否能幫助大眾正確地了解這個世界,並讓公眾就社會事務作出辯論及發表意見。
不少學者及政論家都強調,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必須保持開放及公正。如果傳媒宣揚偏見及隱瞞事實真相,公共空間就會烏煙瘴氣,理性的民意不能形成。公民既不能向施政者進言,也達不到制衡政府的目的,民主政治自然落空。站在施政者的角度,如果傳媒作虛弄假或隱惡揚善,他們也無法了解管治實況及民眾的真正意向,於是無從制訂合乎民情的政策。所以傳媒公共空間的好壞,就成了一個民主社會是否運作良好的指標。
 理想的公共空間必須具備幾項條件。首先它必須公開及自由,公眾能公平參與,自由發言。其次資訊的收集及發放必須完整及客觀,能正確地知會大眾。再者是提供辯論場地,但意見交流必須理性及具批判性。而最重要的,是這個空間保持獨立,不受市場及政治力量的的干擾及操控。在很多西方國家,公共空間遭到廣告及公關等經濟活動的蠶食,而在極權國家,公共空間就被赤裸裸的政治控制鯨吞,經濟及政治干擾是令公共空間不振的主要原因。
理想的公共空間必須具備幾項條件。首先它必須公開及自由,公眾能公平參與,自由發言。其次資訊的收集及發放必須完整及客觀,能正確地知會大眾。再者是提供辯論場地,但意見交流必須理性及具批判性。而最重要的,是這個空間保持獨立,不受市場及政治力量的的干擾及操控。在很多西方國家,公共空間遭到廣告及公關等經濟活動的蠶食,而在極權國家,公共空間就被赤裸裸的政治控制鯨吞,經濟及政治干擾是令公共空間不振的主要原因。
要建立健康的公共空間,公眾必須監察傳媒的發展,防止市場力量的入侵。而為政者也應克制,不要在公共空間插上一手。事實上,如果能保持公共空間理性清明,對公眾、傳媒及政府是三贏局面。有政治智慧的領導人應明白,只有充份了解民意及推行合乎民情的政策,才是鞏固政權的最好方法;摧毀公共空間,對為政者的長遠利益並無好處。
香港傳媒的自處之道
香港大學一位教授曾引述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所說的「我反對你的說法,但我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說明江澤民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就今次事件來看,筆者也認為江澤民有表述他的社會責任論的自由,而香港人也有權提出質疑。
香港政府應就此事和中國領導人展開理性的對話,表述維護公共空間獨立的重要,同時釐清社會責任及國家利益的定義。其實任何地方的傳媒工作者及公民,都會同意傳媒要負擔社會責任及保衛國家利益,問題是由誰去界定何謂社會責任、國家利益及民族大義。香港政府憂慮的是中央政府單方面的詮釋,如果香港政府也有參與界定的份兒,大家就會覺得比較適當。例如香港不少報章社評提出,傳媒做好監察政府的工作,就是盡了社會責任。這個意見若為中國領導人認同,就會減少爭論。當然要取得雙方共識,是需要長時期的對話及互相體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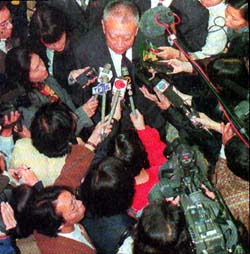 可惜筆者發覺部份香港傳媒近期似乎患上了神經衰弱症,像一頭驚弓之鳥,稍有風吹草動,就慣常性地拼命還擊。這樣未免反應過敏,輕者浪費精力,重者破壞了和中央的關係。當然香港傳媒在保衛新聞自由方面不可鬆懈,但應該避免情緒化,沉著應付,以不卑不亢的冷靜態度回應。
可惜筆者發覺部份香港傳媒近期似乎患上了神經衰弱症,像一頭驚弓之鳥,稍有風吹草動,就慣常性地拼命還擊。這樣未免反應過敏,輕者浪費精力,重者破壞了和中央的關係。當然香港傳媒在保衛新聞自由方面不可鬆懈,但應該避免情緒化,沉著應付,以不卑不亢的冷靜態度回應。
其實江澤民在他的演詞裡談到傳媒時,首先就肯定了要注重新聞自由,顯示他理解到香港人很重視這一點,而且其後在回答記者問題時也顯露了他的克制及禮貌。面對處於強勢的中國領導人,位於弱勢的香港政府一方面立場要企穩,另方面態度應良好,心平氣和展開理性對話。我們很難要求一生受社會主義薰陶的中國領導人放棄他們的社會主義傳媒觀,我們應向他們推介不受政治干擾的傳媒公共空間的優越性,並揭示他們若要真正了解董建華管治實況,就必得依賴傳媒獨立的報導。能做到的話,他們尊重香港傳媒的自由主義式運作的機會也會相應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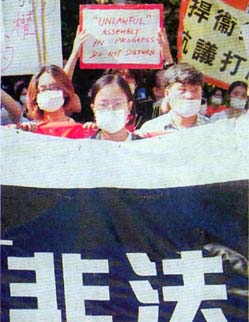 九七以後,香港步入「後殖民時期」。後殖民社會的開始,表示了一個社會陷入新一輪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掙扎。在這個時候,整個社會必須冷靜地反思,尋索在黑暗中緩步前行的路向。在這個歷史交叉點,傳媒的角色很吃重,因為它可以引領社會反思,同時提供辯論的公共空間,讓民眾就政治、經濟和文化轉型交換意見。香港傳媒不喜歡江澤民指指點點,但它們是否也應反省,在過去幾年究竟對後殖民香港作出了甚麼貢獻?對建設健康的公共空間是否有盡力?而在未來又能發揮甚麼正面的作用?傳媒如果做好本身的工作,就能減少外力干預的口實。江澤民說過「悶聲發大財」,看來香港傳媒也應多思改革,埋頭耕耘。
九七以後,香港步入「後殖民時期」。後殖民社會的開始,表示了一個社會陷入新一輪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掙扎。在這個時候,整個社會必須冷靜地反思,尋索在黑暗中緩步前行的路向。在這個歷史交叉點,傳媒的角色很吃重,因為它可以引領社會反思,同時提供辯論的公共空間,讓民眾就政治、經濟和文化轉型交換意見。香港傳媒不喜歡江澤民指指點點,但它們是否也應反省,在過去幾年究竟對後殖民香港作出了甚麼貢獻?對建設健康的公共空間是否有盡力?而在未來又能發揮甚麼正面的作用?傳媒如果做好本身的工作,就能減少外力干預的口實。江澤民說過「悶聲發大財」,看來香港傳媒也應多思改革,埋頭耕耘。


